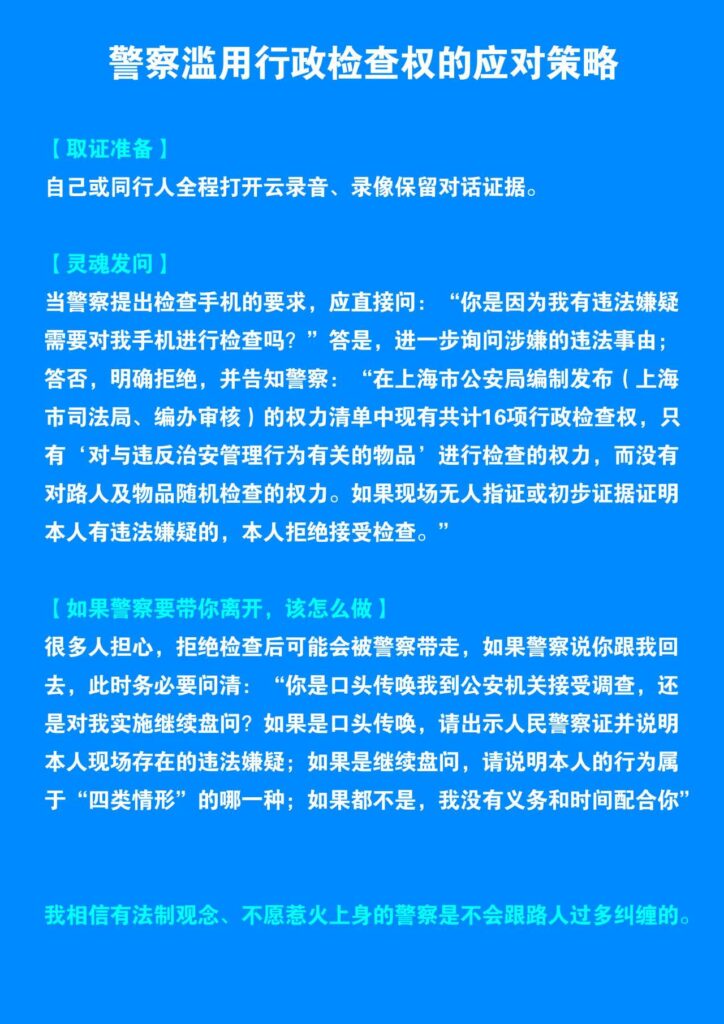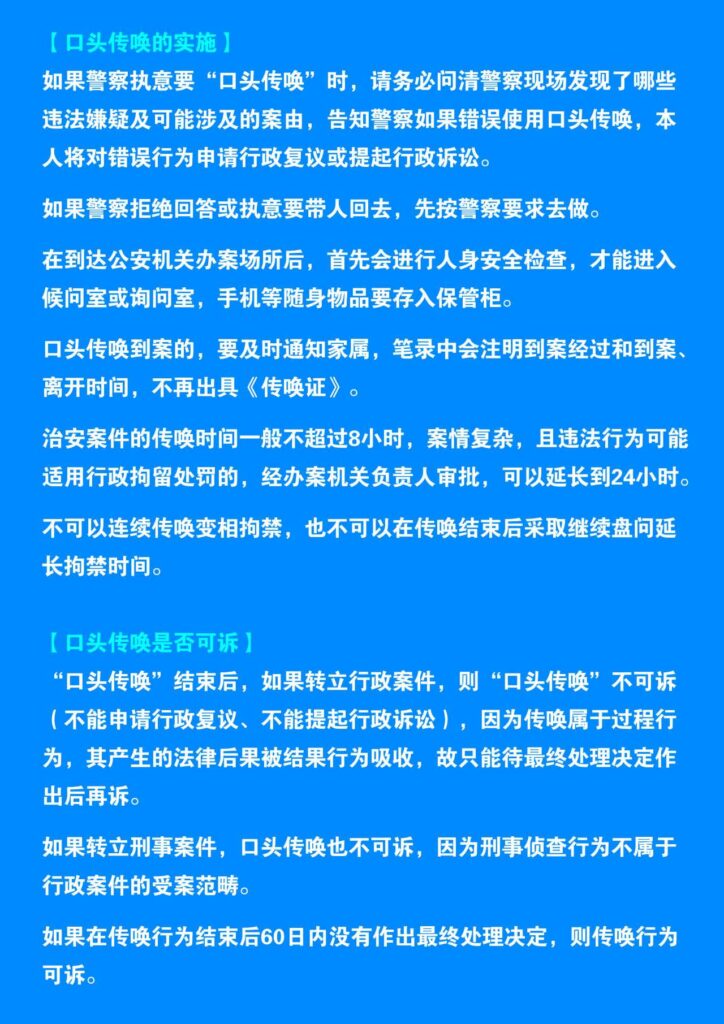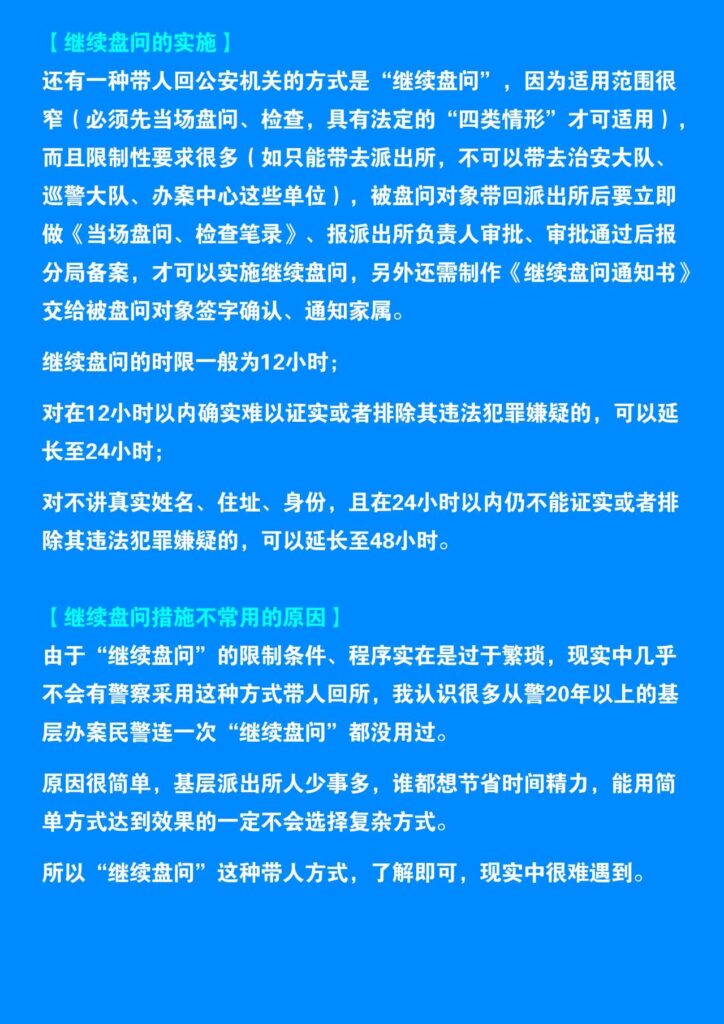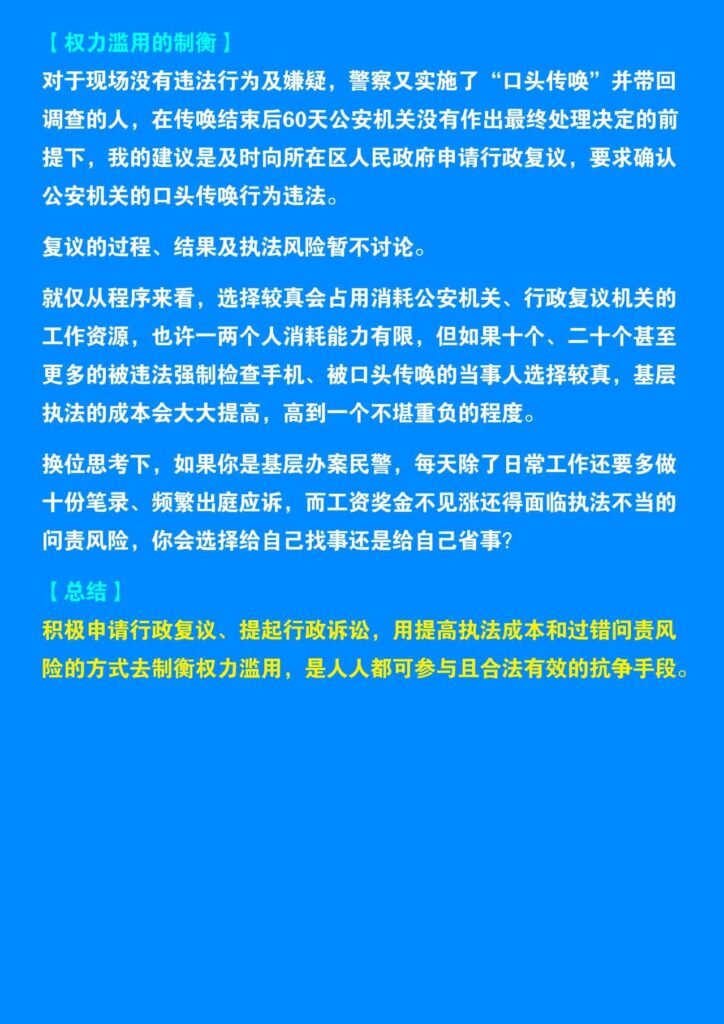仝宗锦
警察对于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建设法治国家责任重大。近来,关于警察能否在地铁、马路等公共场所挨个检查公民手机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一些法律同行,甚至包括并非法律专业的人士也撰文讨论。由于手机在现代社会中对于个人生活、自由和尊严的极端重要性,以及相关问题在行政执法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为法律教员和执业律师,我感到仍有必要继续简单讨论其中的相关问题。
我的看法是:警察不能在诸如地铁、马路等公共场所随意检查不特定乘客、路人的手机。试述如下。
1.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与警察检查手机问题相关的,大致上可以有如下规范性文件:《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法》、《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等等。这些规范性文件按照案件性质和具体适用场合又大致可以分为,涉嫌犯罪的案件进入刑事案件办理程序,例如关于检查、搜查、扣押、封存、提取等等相关规定,涉及违法的案件进入行政案件办理程序,例如行政案件中关于检查、扣押、封存等等规定。但是,除了上述明确区分的刑事或行政案件办理程序之外,法律同时还规定了关于警察现场执法的种种权力。这类权力的行使,并不一定以刑事案件立案或行政案件立案为前提条件。
2.法律为什么赋予警察未经立案即可现场执法的权力,这是因为警察权与诸如审判权等司法权力在性质上存在区别:审判权是被动的,通常来说不告不理,但是警察权乃是行政权力中最主动的权力,它并不限于事后处置,也包含着事前的预防职能。例如,如果一个人携带一个看起来像是危险物品的东西进入公共场所,警察假如先去立案再行检查处置,那显然会贻误时机。各国也都有关于警察现场执法的权力配置。我这学期讲的美国宪法史课程,其中即有1960年代Terry v. Ohio这样关于警察现场执法搜查的案例。由于现场执法的紧迫性及功能需要,在关于警察权配置方面常常难以做到程序上约束的周密和完备,也即“不能管得过死”,因此同时就给警察权的滥用留下大量空间。不过,在我看来,具体到本文所涉问题,警察关于现场执法权力配置和执行中固有的宽松乃至模糊空间,并不能给警察在地铁、马路这样的公共场合随机检查手机内容提供合法性空间,有关行为应属权力滥用,有权机关应予坚决纠正。
3.关于警察在地铁中检查手机内容的事情,公安机关最可能援引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第一款的条文:“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二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七条:“公安机关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可以进行检查。检查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对确有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当场检查,但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该条文虽然对警察检查有关物品设定了一系列程序性要求,但是仍然留了一个口子,即“对确有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当场检查”。因此,问题便在于如何解释警察法第九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七条关于现场执法的相关条文,以及回答,这两个条文是否能够为类似警察在地铁里马路上检查人们手机的行为提供合法性基础。
4.关于《人民警察法》第九条,公安部1995年有一个解释现在依然有效,其内容是:“依照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的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在执行追捕逃犯、侦查案件、巡逻执勤、维护公共场所治安秩序、现场调查等职务活动中,经出示表明自己人民警察身份的工作证件,即可以对行迹可疑、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进行盘问、检查。检查包括对被盘问人的人身检查和对其携带物品的检查。”总结以上,从检查对象而言,警察法规定的是“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公安部将其进一步解释为“行迹可疑、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有违法犯罪嫌疑意味着其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的层面,而是至少在行为上露出端倪,或者像解释所言“形迹可疑”。换句话说,“形迹可疑,有违法犯罪嫌疑”本身意味着待检查对象已经表现出一些实施或将要实施违法犯罪嫌疑的迹象,这里至少有两点:一是待检查对象是特定的具体对象;二是他(她)业已表现出一些涉嫌违法犯罪的可疑之处。以此尺度衡量地铁中对乘客的随机检查,则可以发现,警察的检查对象乃是不特定对象,并且检查对象并未显示出可疑之处。(乘坐地铁是合法行为,本身并不能与涉嫌违法犯罪建立因果关联。)
5.《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七条的有关规定依旧不能为警察的有关行为提供合法性基础。其条文中的“确有必要”虽然给警察的自由裁量权留下大量空间,但是适用至少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二是检查的“场所、物品、人身”与之相关。但是单纯的乘坐地铁或走过马路,并不意味着“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更不能得出手机与该违法行为有关。因此,在地铁或路上随机检查乘客或路人手机的执法行为,显然并不符合上述条件。
6.从《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三版)》关于现场执法的具体行为规范也可以看出有关法律中有关现场执法盘问检查的立法本意并不涉及手机内容。该细则第十一章是关于“当场盘问、检查”,其中11-04一节是关于“盘问、检查的程序”,共分为“表明身份”、“查验身份”、“人身安全检查”、“物品安全检查”、“检查车辆”、“设卡检查”几项。检查手机应属“物品安全检查”事项,有关具体程序规定如下:
“4.物品安全检查。检查物品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1)责令被检查人将物品放在安全位置,不得让其自行翻拿。(2)由一名民警负责检查物品,其他民警负责监控被检查人。(3)开启箱包时应当先仔细观察,注意避免接触有毒、爆炸、腐蚀、放射等危险物品。(4)按照自上而下顺序拿取物品,不得掏底取物或者将物品直接倒出。(5)对有声、有味的物品,应当谨慎拿取。(6)发现毒害性、爆炸性、腐蚀性、放射性物品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时,应当立即组织疏散现场人员,设置隔离带,封锁现场,及时报告,由专业人员进行排除。(7)对违禁品,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予以扣押或者收缴。(8)避免损坏或者遗失财物。
从上边列举关于“物品安全检查”的具体程序规范可以看出,人民警察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现场执法的检查物品,事实上主要是对其安全性方面的检查,而并不涉及对于手机这样日常的非危险物品具体内容的实质性检查。关于手机内容的检查,实际上是关于电子数据的收集程序,至少包括扣押、封存、提取等等具体步骤,需要保证电子数据收集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警察未经合法的办案程序检查手机内容,不仅影响收集的合法性问题,也同时涉及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问题。
7.警察在地铁、马路这样一般的公共场所上检查不特定对象的手机,要求其解锁手机并对手机内容进行检查,哪怕碰巧遇到个别对象的手机中正好存储有某些违法软件或信息,实质上也意味着某种让当事人“自证其罪”的行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第八条都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虽然在行政案件的办理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一原则,但是让检查对象解锁手机并查看,依然违反了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
8.随着现代社会信息网络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对于个人生活、自由、隐私、尊严等等方面的意义自不待言。如果采用类似的撒网方式针对不特定对象开展执法检查,并允许警察随意检查不特定对象的手机内容,哪怕侥幸查到个别违法犯罪行为,也完全违反了比例原则。事实上,由于手机内容直接事关宪法上通信自由和秘密等基本权利,有关宪法条文已就此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也就是说,实际上,宪法将针对手机内容的检查限定在“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两个方面,这甚至能够推论出即便有“违法行为”嫌疑,那也不能直接检查手机内容。当然,反对者可能说,上述宪法条文的“追查刑事犯罪”并不必然意味排除了违法行为。那么我要说,宪法关于“违法”和“犯罪”是有语词上的区分的,在第四十一条中有“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而更为明确区分的证据是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民警察法等相关法律虽然规定了现场执法,包括警察检查物品的有关权力,但是其检查对象应是“形迹可疑,有违法犯罪嫌疑”特定的人,而不能针对地铁乘客、马路行人这样的不特定对象。甚至,由于宪法条文的明确规定,针对违法嫌疑的人员,甚至根本不能以检查手机内容这种侵入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方式予以执法。同时,让公民解锁手机实质上意味着让公民自证其罪,并不符合刑事法或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由此,警察如果对不特定对象随意检查手机内容,当属滥用职权行为,理应得到有权机关的纠正。